在困頓的環境中,古巴老樂手仍展現生命的活力。

聲音有開始就有結束,這轉瞬即逝的音樂似乎暗示著人生的根本事實,即生命的有限性。
經歷過耳疾折磨的貝多芬,至1802年10月寫下畢生都未寄出的海里金史塔遺書之後,幾乎同一時間創作的c小調第三號鋼琴協奏曲,其中不僅有悲愴命運的感傷,但更多的是昇華與重新再出發:我們在最終的第三樂章中,可以非常清楚感受到,貝多芬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生命的幽谷。而就像在此之後的貝多芬,其第三號英雄交響曲與第七號交響曲裡,象徵死亡元素的「葬禮進行曲」,都出現在第二樂章而非終樂章,實非偶然。在這些音樂裡,他想傳達的是:從黑暗走向光明的過程中,悲傷是暫時性的,透過音樂,現世生命更有其積極意義。而就像許多人在貝多芬歌劇《菲岱利奧》或在其第五號命運交響曲最後,強烈感受到,作曲者不希望樂聲的最終結束,一直在肯定著某些東西,拖延或避免結尾的到來。但我們都很清楚的現實是,無論如何拖延,樂聲終究無法避免結束。

貝多芬是美學自主的音樂原型
樂聲一定會終了,生命一定會結束。面對這樣無可避免的必然結果,人究竟該如何活過這有限的一生。是逃離或是直面。
(一)消極逃離變容
沒有音樂的生命將是一個錯誤,尼采如是說。因為人生不僅有限,而且幾乎去日苦多,現實世界是這樣粗礪與充滿不公。在眾多的藝術領域裡,雖然音樂可能最不為人所知性理解,但卻恰恰相反地,最為多數人所感性聆聽。事實上,發自內心對音樂的感性感動,幾乎完全不需要理性的清楚認知,而這正是音樂最為獨特之所在。音樂常為人們提供消極逃離的寄託所在:在極度的悲傷與幾乎難以承受的痛苦中,音樂可以撫慰人心帶領我們走向世界本然的核心、生命意志的心房。
一個令人「驚訝」的人性現實是:在今天巴勒斯坦人倉皇無助的臉龐上,彷彿時光倒轉地看到納粹集中營裡猶太人瘦弱無奈的表情;同樣地,在冰冷傲慢的以色列官員的言行中,也讓我們同樣覺察想像,當時蓋世太保不可一世的可怕翻版。確實,悲劇若一再重演,就變成了鬧劇。而令人更感挫折的是,以、巴衝突僅是人類普遍政治寓言的顯例之一,這個世界幾乎到處都在上演著同樣的戲碼,或輕或重。這裡,我們也同時想到那位惹內,那位幾乎是西方知識界第一位膽敢公開表明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與同情。在那1970與1980年代的氛圍裡,巴勒斯坦被等同於恐怖主義,選擇站在巴勒斯坦這邊,是最危險的政治抉擇[1]。然他卻在著作也在自己的生命行動中,烈焰般燃燒著對包括巴勒斯坦人等所有受壓迫種族、階級的關注與支持;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對照是,惹內日常生活的應對卻幾乎是絕對的沈默、孤獨甚至「寧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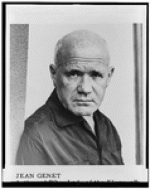
敢為巴勒斯坦人說話的惹內
在這驚訝(surprise)與寧靜(serenity)的沈思中(如顧爾德所說的,這是他一生的藝術目標),音樂如何引領我們走向生命的真實脈動。
1. 貝多芬的突兀疏離
對比於莫札特的窮困潦倒至死,貝多芬開始懂得賣樂譜維生,這象徵著靠個人才華的資產階級日漸取代世襲封建階級的社會開端。一個資產階級,終於能夠毫不羞赧地像過去王公貴族般自信且高傲地說話。然貝多芬之所以讓人尊敬的地方,正如阿多諾在其貝多芬研究中所說的:他不僅是革命資產階級的音樂原型,他同時也是一種擺脫社會監護,在美學上充分自主,不再是僕人音樂的原型。也因此,當如此美學自主的音樂原型,在意識到被當時社會全盤接受並利用以致靈光消逝之際,其最後期音樂所呈現的,會是令周圍的人感到「驚訝」無所適從,猶如溝紋處處充滿裂隙、未經修飾轉化的暴躁手勢風格。如此之對新的資產階級秩序的晦澀拒絕,其實是他作為一個純粹音樂藝術家的最忠實表態與自我完成。

貝多芬晚期風格是未經修飾的暴躁手勢
應是那首降B大調的第13號弦樂四重奏:其中第五「慢板」樂章,其沈痛的抒情淒美旋律,述說著晚年貝多芬對其一生的回憶;而之後為了緩和這幾乎難以承受的悲傷情緒,緊接的終樂章是令人驚異、艱深龐大的「大賦格曲」[2]。那是貝多芬回顧其一生對個人主義奏鳴曲式的宣揚,在最後向著兼顧他者的賦格曲式的回歸;當然,其風格揉含奏鳴曲式的賦格,已與巴哈時代的賦格大異其趣。

「大賦格曲」後來貝多芬還改編了鋼琴四手聯彈版本
2. 在晚霞中的理查.史特勞斯
從貝多芬到史特勞斯,確實是百年以上的經歷。1945年5月7日德國終於宣告無條件投降,史特勞斯得知消息後,電台立即播出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中的「送葬進行曲」。而一如後來史特勞斯所說,那一刻的貝多芬音樂讓他有極深的感觸,同時也與他手邊的作品「變容」密切相關。
事實上,正如這首為23位弦樂獨奏者而作的「變容」,其草稿簿上有著「為慕尼黑守喪」的題字,「變容」被薩依德稱為是「晚期風格的百科全書式作品」,這確實是一個親身經歷歐洲輝煌與傾頹的史特勞斯「蛻變」。「變容」一詞來自歌德的啟示,晚年的歌德以此來形容自己在知性方面的發展,樂觀且向陽;然此時的史特勞斯,卻是在貝多芬「送葬進行曲」的主導下,詮釋世界的變容到頭來依然走入葬禮行列的情景。面對著所處世界的劇變,特別是得知家鄉慕尼黑國立劇院全毀的消息,史特勞斯無可奈何地朝向18世紀的回歸與逃避寄託。

理察.史特勞斯
應是那「最後四首歌曲」(之後發現還有一首「葵花」)所呈現的「寧靜」心境。前三首「春天」、「九月」與「進入夢鄉時」是根據赫塞的詩寫成,呈現季節時序與個人的疲憊;而第四曲「在晚霞中」則是依據艾辛多夫的詩譜成。這是一位84歲老人,歷經風霜(他還經非納粹化審判獲判無罪)後展現生命厚度的最後天鵝之歌:「在晚霞中」最後,當歌者朗誦般唱出「難道這就是死亡?」之後,管絃樂以寬緩的降E大調緩緩結束時,我們很難不感受到一種昇華後的崇高悲哀。

著名的最後四首歌版本
(二)積極直面蛻變為爵士樂團如何
絕大部分的貝多芬作品,在任何威權社會下演出,都有其隱含的反抗與呼喊自由的緊繃對立;同樣地,象徵彼此對話和諧共鳴的「西東詩篇管絃樂團」的存在與演出,在今天以、巴衝突中,也都飽含著對周遭暴虐的無言抗議。2008年該樂團被賦予聯合國和平大使任務,巴倫波因更在當年國際人權日前夕,直稱「西東詩篇管絃樂團」為「主權獨立共和國」,並告訴大家,其團員的相處模式足堪中東地區所有國家的楷模。
如今,樂團在沈重的「命運」演出以及不斷地向以色列叩關與阿拉伯國家挑戰演出之餘,未來,其實應有更多的可能發展與蛻變。眼前費力挑戰的積極直面當然必需繼續;但每個團員(延伸可至中東地區的每個人)個人生命意義的提昇,也必須以另一種輕盈的激盪來創造。從而,外在大世界的奮鬥與內在生命意義的探尋,才能得到完美適當的聯結。
在樂團中,一直以來巴倫波因主導的角色非常明顯,也許在這樂團的前十年實屬必要。於今他是否應思考退居幕後第二線,漸漸淡化樂團的指揮權威地位,而慢慢蛻變為類似的爵士樂團,這或許是號稱「主權獨立共和國」的樂團,最終能讓每個團員皆有平等發揮空間的未來選項之一[3]。爵士樂團和交響樂團的演奏的確有以下明顯差異:因為爵士樂手在很大的程度上,除了必須與他人和諧共生演奏外,但也都有機會很自由地去表現他想要的自己。因此如果說:巴哈音樂所彰顯的賦格對位精神,是發自音樂作品內在地關照他人;那麼,現代爵士樂團的演奏模式則是在這之上,更加外在地關照他人。而這從內而外平等地與他人連結對話,同時也都是每一個人的自我完成。
著名的文學理論家伊格頓在其近著《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中,滌識盪相最後竟也認為,爵士樂團是美好人生意象的最佳選擇因為那是彼此激盪襯托、對等互惠的一場無目的樂趣的即興演出。事實上這樣的說法,某種程度也呼應了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的識見:酒神戴奧尼索斯的感性歌聲嘉年華回歸,可以緩和日神阿波羅的理性討論辯證術在當代的過度發展。
此刻自然地,從「西東詩篇管絃樂團」聯想到那部描寫古巴老樂手的紀錄片《樂士浮生錄》:一樣都是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下焠鍊而生,但也一樣散發出驚人的生命力。在美國對古巴長期的封鎖禁運下[4],這個傳奇古巴樂團Buena Vista Social Club在1998年藉由音樂製作人Ry Cooder與導演溫德斯的重新發掘,其表演風采得以淋漓盡致展現。特別是紀錄片中,那兩場分別在阿姆斯特丹卡列劇院與紐約卡內基音樂廳的經典即興表演,讓我們知道即使在最艱困的環境下,藉由音樂的喜好與沈醉同樣也能展現生命的美好,而且是每一個團員都可以擁有的,屬於自己的絢麗時光。

[1] 在阿爾及利亞對抗法國過程中,身為法國人的沙特非常有勇氣地選擇站在阿爾及利亞那邊;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害怕被指責為反猶主義,他在以、巴衝突中卻選擇強烈支持以色列。
[2] 在樂譜銷售與冗長艱深的考量下,貝多芬可說是在生命的最後,重新譜上新的第六樂章才辭世的。
[3] 當前指揮家對團員的權威形象與不成比例的偏高薪水,在在都使一般團員不快樂,團員大多感覺僅是指揮的工具。就如薩依德引述阿多諾所描述的托斯卡尼尼的指揮形象,是由典型現代企業所創造出來的,壓縮並控制音樂的表演。巴倫波因某種程度不可能完全擺脫這樣的指揮家框架,所以,這「主權獨立共和國」樂團目前有一個沒有任期限制的強勢總統。
[4] 2009年4月17日,美國總統歐巴瑪出席美洲高峰會。在古巴主動提議修補長達近半世紀的敵對機緣下,歐巴瑪回應承認美國過去在這地區的錯誤政策,他並希望與古巴建立新的開始。這項談話意味著,美國對古巴的長期禁運封鎖可能即將結束。
